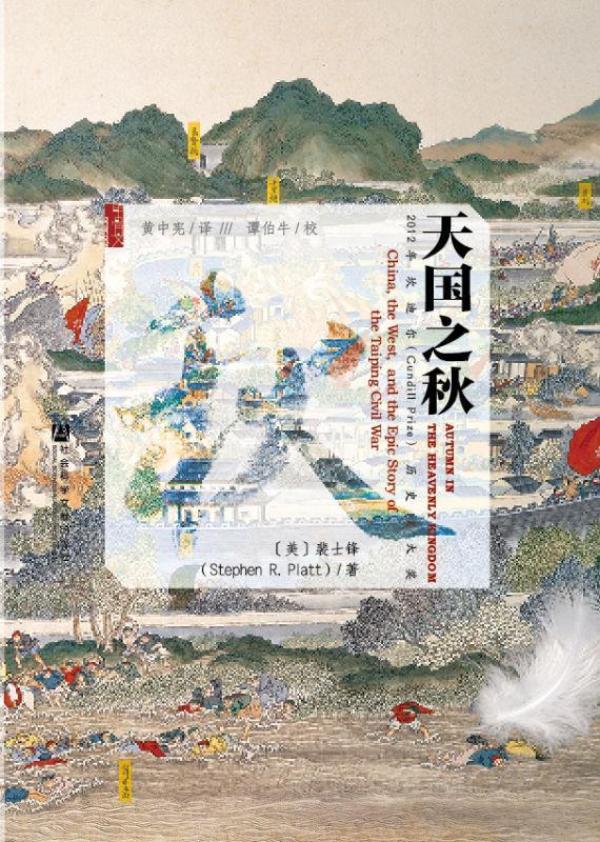编者按:欧洲1848年革命、太平天国运动、美国南北战争……19世纪中叶,世界不同大洲发生的这些重大事件看起来毫无关联,但又似乎存在着某种隐约而深刻的纽带。在《天国之秋》中,美国历史学家裴士锋将太平天国运动置于全球视野中,用引人入胜的人物故事为这段熟悉的历史提供了另一维度。该书第一章以瑞典传教士韩山文与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的友谊切入,展现了西方人对太平天国的最初认识,以及欧美媒体在该运动和同时期国际事件之间找到的联系。该书在2012年获坎迪尔历史奖大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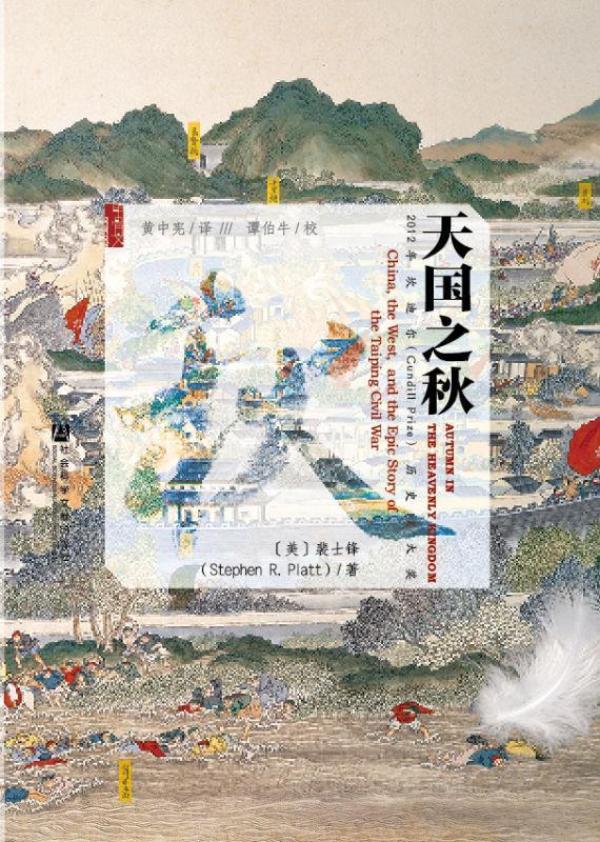
一八五二年的香港是个潮湿和疾病肆虐的地方,是大清帝国南方海岸外的多岩岛屿。有人说岛上“到处开挖土地释出瘴气”,岛上居民终日害怕瘴气缠身。山与海湾之间坐落着小小的英国人聚落,但翠绿与湛蓝的山海风光使人看不到表象底下的阴暗。香港的主要街道,街名散发着思乡情绪(皇后大道、威灵顿街、荷里活道),货栈、兵营、商行紧挨着矗立其间。离开这些建筑,走上从海岸通往山丘的石子路,能看到最壮丽的景致,但走不久即离开白人聚落,触目所见是散落于水稻田和甘薯田之间的华人房舍。自十年前英国人靠着鸦片战争拿到这座岛屿当战利品之后,这一农村景致一直没变。有些较有钱的商人在那些山丘上盖了豪宅,宅邸中呈阶梯状布局的花园将山下的港湾和城区尽收眼底。但这些大宅的主人好似离开香港的保护圈太远,宅中居民于是生病,然后死亡。这些阴森森的宅邸被冠上“热病屋或死人屋”之名,静悄悄地坐落在山间,人去楼空,像是空洞的眼神在冷冷审视着山下的移民。
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是那些移民之一。他是瑞典籍的年轻传教士,薄薄的络腮胡衬出他秀气、几乎女孩子气的五官。他天生有着迷人的嗓音,年轻时在斯德哥尔摩曾与“瑞典夜莺”珍妮·林德(Jenny Lind)同台合唱。但林德继续走歌唱之路,风靡欧美歌剧院,令肖邦与安徒生之类仰慕者拜倒在她石榴裙下时,韩山文的人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折。他雄浑有力的男高音,在讲道坛上找到注定的发挥舞台,一八四七年离开故乡瑞典,坐船来到地球另一端,疟疾横行的香港,心里只想着要以另一种方式让中国人臣服。
韩山文本来大有可能默默无闻度过一生,因为他最自豪的成就,在小小的新教传教士圈子以外没人看在眼里。他是他那一代最早勇闯中国乡间的欧洲人之一。他离开较安全的香港,到中国商港广州之外,珠江更上游一百六十公里处的一个村子传教(但后来基于健康考量,他还是回到香港)。他也是第一个学会客家话的欧洲人。客家人是吉卜赛似的少数族群,在华南人数颇多。若非一八五二年晚春某日,有位因他而皈依天主的乡下人带了一个客人来找他,他这一切努力大概得不到世人多大重视。那是个矮小圆脸的客家人,名叫洪仁玕,有着一段精彩的人生经历要说。
韩山文忆起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说这个客家人最让他奇怪的地方,是他似乎已非常了解上帝和耶稣,尽管他来自离香港传教士狭小的活动范围很远的地方。韩山文带着好奇,听洪仁玕讲述使他踏上香港的众多机缘,听得一头雾水。他说到异梦和战斗,说到由信徒组成的军队和礼拜会,说到一名客家人出身的先知。他被清廷差役追捕,易名到处躲藏,至少他是这么说。他曾遭绑架,然后逃脱,曾在森林里住了四天,在山洞里住了六天。但这一切听来太光怪陆离,韩山文坦承:“我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他不知道洪仁玕说这些遭遇的用意,于是请洪仁玕写下来,洪仁玕照做,然后没说什么就离去——韩山文原以为他会留下来受洗。韩山文把洪仁玕写下自身遭遇的那叠纸放进书桌抽屉,将心思摆在其他事情上。此后将近一年,他没把这些纸放在心上,直到一八五三年春得知南京已成血海,韩山文才意会到洪仁玕粗略交代的那些怪事,意义超乎他想象。

洪仁玕到天京担任军师初时上奏天王洪秀全陈述他向西方学习草拟的建国方案。视觉中国 图***
韩山文跟香港及上海的其他移民一样,完全是透过零星含糊的传闻,得知中国境内情势日益动荡。从中国的政府公文,似乎看不出一八五○年代初期日益加剧的混乱有什么模式,看不出存在什么原则或势力集结之处。中国乡间的地方暴乱和小股盗匪横行,始终是帝国当局的困扰,谈不上是新鲜事或值得一顾,尽管在鸦片战争后这几年,这类事的确变多了。深入中国内陆的本国旅人和秘密(传教)的天主教神甫传言:有个更大的运动团体出现,那个团体由名叫“天德”的人领导。但许多传闻说那人已经死在官兵手里,或说根本没那个人。在没有明确消息下,沿海港口的洋人对这类事情不大关心,只担心土匪使茶叶和丝的生产停摆。
但一八五三年南京城的陷落,把一场庞大内战直推到上海租界的大门前。上海位于长江出海口,距更上游的南京只约三百公里。五十万名自称太平天国的叛军,从华中搭乘大批征来的船,浩浩荡荡涌向南京,所过之处,城市变成空城,政府防御工事变成废物。情势非常清楚,这不只是土匪作乱。上海人心惶惶,与南京的直接通信断绝,情况混沌不明(美国轮船“苏士贵限拿”号〔Susquehanna〕想溯江而上到南京查个清楚,结果搁浅在路上)。谣传叛乱分子接下来会进军上海攻打洋人,上海县城里的本国居民把门窗封死,收拾家具,搭上河船或逃到乡间避难。洋人仓促着手防御,临时找来一批志愿者组成防守队守城墙,并备好几艘船,打算情势不妙就上船离开——两艘英国汽轮和一艘双桅横帆战船,还有供法国人与美国人搭乘的汽轮各一艘。
但太平军到南京就停住,至少目前是如此。太平军并未进军上海,上海警戒解除。叛军把矛头朝北,指向满清都城北京,以南京为作战基地,掘壕固守,准备打一场漫长且惨烈的战役。他们把南京改名“天京”,天京距上海不近又不远,令上海洋人想一探究竟。一八五三年四月下旬,就有艘英国船排除万难抵达南京,但带回来的南京动态消息却相互矛盾。最明确的看法出自英国全权代表之口,他宣称太平天国拥有由“迷信与胡说八道”构成的意识形态。那些去过的人对叛军的出身一无所悉。
尽管欠缺明确的讯息,有关中国内战的第一手陈述还是从上海和香港往外传,引起西方世界的注意。欧洲刚在五年前经历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巨变,中国的动乱似乎与之有明显的相似之处:悲惨的中国人民,遭满人主子欺压,如今终于挺身要求改变。《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称那是“与最近欧洲所遭遇者类似的社会变动或动乱”,说“亚、欧同时发生类似的骚乱,史上绝无仅有”。由此可见,地球另一端的帝国如今和西方的经济及政治制度有了联结。
一八五三年担任《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伦敦通讯记者,正埋头理清他对资本主义之看法的马克思,也认为中国这场叛乱表明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称它是英国在最近的鸦片战争中强迫中国开港通商的最终结果。照马克思的说法,中国正发生的事,不仅是叛乱或数场暴动的合流,而且是“一场令人赞叹的革命”,那革命表明与工业世界的息息相关。他甚至主张,正是在中国,可以看到西方的未来:“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欧洲人民的下一场起义,他们下一个为了共和自由与廉洁政府的运动,其成败或许更可能取决于目前在天朝上国——与欧洲完全相反的国度——发生的事,而较不可能取决于如今存在的其他任何政治原因。”
诚如他所说明的,中国这场动乱肇因于鸦片贸易;十年前英国用战船强行打开中国的市场,从中削弱了中国人对其统治王朝的“盲目相信”。他深信,与外面世界的接触将摧毁旧秩序,因为“腐烂必然随之发生,就像任何细心保存在密封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旦与室外空气接触,就必会腐烂一样”。但受清朝腐烂影响者,不会只有中国自己。在他看来,整个太平革命是英国所造成,而英国海外作为的影响,如今将回传到国内;他写道:“不确定的是那场革命最终会如何反作用在英格兰身上,并透过英格兰反作用在欧洲身上。”
马克思预测,中国市场落入太平革命团体之手,将削弱英国的棉花与羊毛出口。在动乱的中国,商人将只接受用金银条块换取他们的商品,从而使英国的贵金属存量愈来愈少。更糟糕的是,这场革命将切断英国的茶叶进口来源,大部分英国人所嗜饮的茶叶,在英格兰的价格将暴涨,同时,西欧境内的农作物歉收看来很可能使粮价飙涨,从而进一步降低对制成品的需求,削弱英国经济所倚赖的整个制造业。最后,马克思断言:“或许可以笃定地说,这场中国革命会将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已然(火药)过载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然后在往国外扩散之后,紧接着欧陆会爆发政治革命。”
如果说马克思一心想让《纽约每日论坛报》的读者相信,这场中国内战是与欧洲境内的运动类似的阶级斗争和经济革命运动,那么美国南方奴隶港新奥尔良的《每日琐闻报》(Daily Picayune)的主编则从他们自身的世界观出发,以大不相同的角度看待这件事。诚如这些主编所认为,这是场种族战争,中国是剧变中的奴隶国。他们解释道,太平军发迹于广西和广东这两个南部省份,两省居民“基本上是中国原始种族”。相对地,北方的满人是“中国的统治种族”,自两百年前入主中国之后,“中国一直被其主子当成受征服国家来统治”。他们解释道,这两个种族从未混合,然后,与他们的美国南方观点,也就是以奴隶为基础的和谐社会观相一致的,该报表示,在中国,“不多言、有耐心、刻苦的数百万人,以足堪表率的温柔敦厚,接受他们主子的统治”。这个主奴和平共处的满汉国,唯一威胁其稳定的是这些不愿接受宰制的华南“原始”人。于是,太平叛乱与美国黑奴的暴动,有了令人神伤的相似之处。
伦敦《泰晤士报》(Times)最有先见之明,立即抓住问题核心,探讨英国是否该派海军投入这场中国内战,以及如果这么做,该站在哪一边。在一八五三年五月十七日,也就是南京陷落的消息传到伦敦后不久,《泰晤士报》某篇社论指出,太平天国似乎所向披靡,“据各种可计算的概率,他们会推翻中国政府”。《泰晤士报》还转载了上海某报的一篇报道,问道“换人当家做主”是不是大部分中国人所想要,并表示太平天国虽然在华北不大受喜爱,却代表了一股汉人所乐见的改变力量,“认为不该再忍受官员横征暴敛和压迫的心态,似乎在全国各地都愈来愈浓”。到了夏末,《泰晤士报》直截了当宣告,中国这场叛乱“就各方面来看,都是世人所见过最大的革命”。
但叛军本身却是个谜。《泰晤士报》的读者会轻易断言,太平天国得到汉人的支持——至少得到勉强的支持——准备推翻满人,开启新政。但该报主编也就英国的无知发出告诫之意。“关于叛乱的源起或目标,我们没有具体的讯息,”他们写道,“我们知道现在的中国政府可能在内战中遭推翻,但就只知道如此。”他们忧心英国不够了解叛军的本质或意识形态,而无法决定该不该予以支持或鼓励:“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无法断定我们的利益或职责该落在哪一边——这场叛乱有正当理由或无正当理由,前途看好或不看好;民心向背如何,或它的成功会促成我们与中国人的关系往好或往坏的方向改变,或是否会促成改变。”但事实表明,其中最迫切的问题——叛乱的根源、太平天国是什么样的组织、他们的信念为何——答案将在香港寻得。答案就潦草写在几张纸上,而那些纸就塞在韩山文书桌的抽屉里。